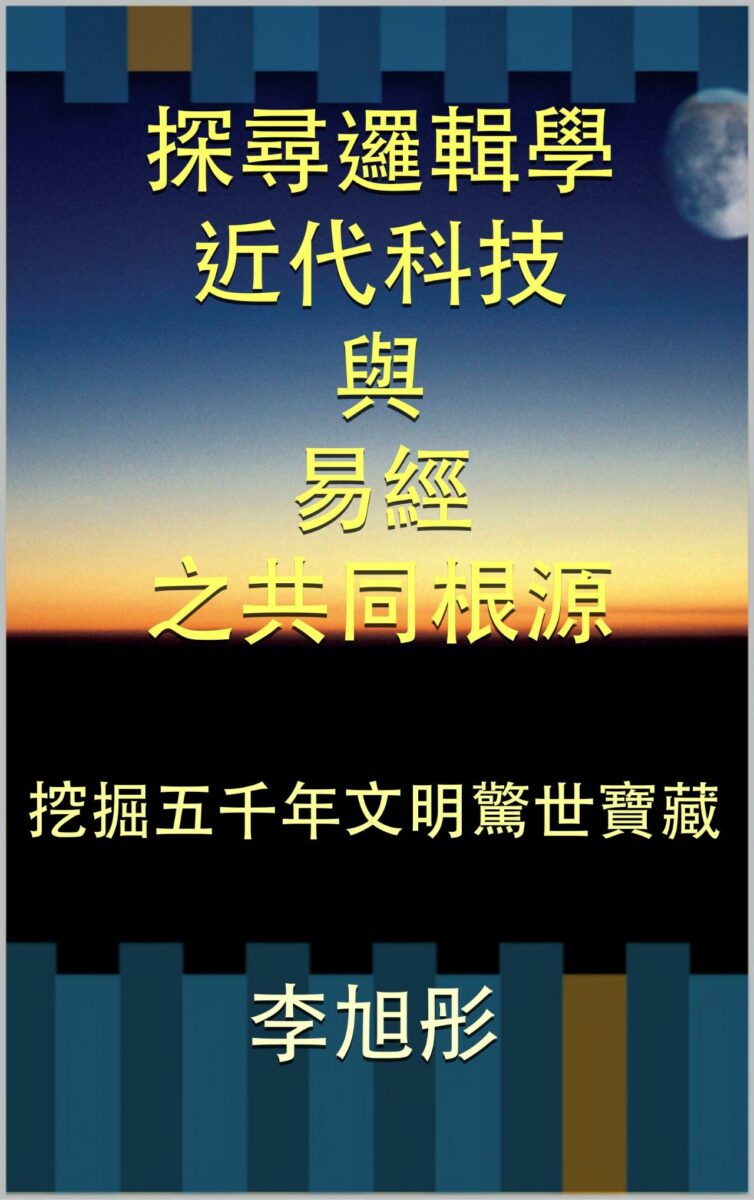【2020年11月18日】在张子静曾是一个少年时,和他后来的生命晚期,都写过“我的姊姊张爱玲”这样的同类文章,晚年接受记者采访谈张爱玲。他很忠厚,回忆起父亲、母亲、姐姐,一律都有温暖底色。同样,他抱歉着自己这样平庸而寒苦的一生,实在是配不上那样才情飞扬的姐姐。然而,他以她为骄傲。
“我弟弟实在不争气,因为多病,必须扣着吃,因此非常地馋,看见人嘴里动着便叫人张开嘴让他看看嘴里可有什么。病在床上,闹着要吃松子糖——松子仁舂成粉,掺入冰糖屑——人们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到嘴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擦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
“我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也不。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长辈就爱问他:’你把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口回绝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么?’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像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我叫月红,他叫杏红,我使一口宝剑,他使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咚咚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我弟弟常常不听我的调派,因而争吵起来。他是’既不能令,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
这是张爱玲的散文里的弟弟,在她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她是爱着弟弟的。童年时,目睹后母打弟弟,她流过何其多的眼泪。然而,弟弟生来就不如姐姐那么特立独行,父母离婚后,他不像姐姐,有姑姑和母亲可以投奔,他是个男孩,只能在家里和父亲在一起,总是在夹缝里求生存,没有道理可以理论的,因此养成了软弱和迷糊的个性。曾经,张爱玲看着后母打弟弟,父亲也打,然而,弟弟并不记仇,这夫妇二人对躺在榻上抽鸦片时,弟弟偎依在他们身边,如一只偎炕的小猫,神情心满意足。这样的情景,一如她看着弟弟挨打,那样令她心灵震颤。曾经的那种“一定要报仇”的心意,也渐渐成了个笑话。弟弟是个没有心气的混沌人,他软弱,得过且过,随遇而安,因为没能力反抗,为着生存,这个懦弱的孩子脾气好得不得了,同时呢,也含糊和分不清是非。而张爱玲的性情,按照胡兰成的鉴定——最是狠毒、绝决的。她渐渐看不上弟弟。
在散文《私语》里她写道:被父亲囚禁半年后,她逃出了家,投奔母亲。她对着浴室里梳妆的美丽的母亲哭泣道:“要接弟弟来,送他去学骑马……”后来,弟弟也不堪父亲和后母的凌虐,学着姐姐逃到母亲这里来了,随身“带着一双用报纸包的球鞋。”弟弟哭着,张爱玲也在一边哭着,请求母亲收留下弟弟。然而,我们前文说过了,在那个阶段的黄逸梵,心事都在社交和男女纠缠上,她没有多少母爱给这一对和前夫生下的儿女。于是,做母亲的以公事公办的口吻向弟弟解释,她和他们的父亲已经离婚了,她负担不了两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于是弟弟依然回去父亲和后母的家,“他流着泪,带着他那双报纸包的球鞋。”——那种孩童的孤苦伶仃,流落无依,格外地跃然纸上。我每次读到这个细节,都会油然地泪盈满眶。
然而,张爱玲也记恨着儿时的一张水彩画,被人力透纸背地打了横杠——是弟弟干的;后来后母嫉妒她频频去探望生母,从中生事,宣扬她打了她,她得了忤逆犯上的罪名。这个阶段,她偶然在弟弟抽屉里看见一封信,弟弟写着“家姐事……家门之玷”——他在学着经理人事,于是给一位堂兄弟写了这么一份信,寄出与否不得而知。但张爱玲对此事,铭记在心,她被伤到了。 《小团圆》里,她反反复复提及,反反复复地写。
再大一点,弟弟的立场就渐渐地偏向后母了,凡事替后母说话,认为是父亲糊涂,这个后母是好的。在姐姐这里,他的混沌简直是无可救药的了。到末了,她对他连同情都没有了。他每每开口讲话,踌躇满志地计划“去做套西装穿穿,再去找个事做做”——九莉就蹙眉强笑着道:“你不要再说了呀。”在一篇短文里,她还提及过,上海小市民的滑稽和心酸:好容易做了套西装,然而,共产党来了——西装派不上用场了。
后来,张爱玲在美国时,在英文小说《易经》里,迳直把这个角色,写成早夭了。他的生命在她看来,实在是没价值的。
姑姑从前也和张爱玲一样,在这个弟弟还很漂亮很幼小的时候,喜欢这个小男孩,出门时常常和弟弟开玩笑,商量道,把你的眼睫毛借给我一晚上好不好?因为弟弟生得好看。然而,在张子静的回忆文章里,对姑姑的印象是十足冷淡无情的:“不过姑姑对我始终有不同的看法,比较冷淡。她认为我一直在父亲和后母的照管下生活,受他们的影响较深,和她及我姐姐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因此对我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和距离。她们还住在爱丁顿公寓时,一次我去看姐姐,两人说话的时间长了些,不觉将近吃晚饭的时分。我姑姑对我说:’不留你吃饭了,你如果要在这里吃饭,一定要和我们先讲好,吃多少米的饭,吃哪些菜,我们才能准备好。像现在这样没有准备就不能留你吃饭。’我只好匆匆告辞。”
对此,张爱玲在《小团圆》当中这样替姑姑的冷口冷面的狠心做解释:“他小时候有一次病重,是楚娣连日熬夜,隔两个钟头数几滴药水给他吃。九莉也是听她自己说的。但是她这些年来硬起心肠自卫惯了,不然就都靠上来了。”——舐犊之情从前是天然都有的,只是世态炎凉,一层层灰一层层沙搀下来,积累得久了。那点真心都埋没了。
而在《小团圆》里,张爱玲写到她家的那些原籍安徽的仆人,李鸿章的乡亲们。那些乡下人还保存着一个人伦常理的乡村社会的秩序,有帮扶有依靠的。夜晚的厨房,长年横七竖八的睡着人,有一回,奶妈的儿子来上海找个糊口的工作,每天晚上坐在灶门口,由奶妈将残羹剩饭热了来吃,夜里则睡在厨房地板上,如此,也是住了半年。这样的细节,想来是刺激张爱玲的。因为这些穷苦的乡下人之间,保存着最本质的舐犊之情,乡情伦理。而这些做主人的,虽然饱读过传统经纶,可是传统习气全无,旧日的传统伦理统统丢弃,信奉西来文明最表面最冷酷无趣的那一套,每一分钱的账目都算得清清楚楚,要多占点好处是绝对不能的,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做出最无情的表情,哪怕是面对这个一无所有,是父母辈所有故事情节的最直接受害者的小男孩,他没有能力害任何人,可是,所有的人都蔑视他,认定他糊涂,拎不清。尤其是他没有财产,没有倚靠,什么都没有。
张爱玲离开上海,约好和姑姑互不通信。她们都是洞察时事的人,唯有张子静,混沌地奔走谋生,做父亲的当年为着守旧,也是不肯花钱,不肯送儿子去上新式学校,而是一直把他留在身边请私塾先生教课,当然,他的钱也不曾让儿子看见,自己和妻子都吸鸦片,夫妇俩合伙花光了所有的钱,再加上投资失利等等缘故,在1948年已经穷了下来,不再有花园洋房和仆人,晚年栖身在一间房间里,和人合用厨卫。同样是因为省钱,夫妻装聋作哑地,从来不提给张子静娶亲结婚这桩人生大事。张子静在扬州等地谋生,后来又在上海远郊的中学教书,虽然这唯一的儿子并不曾被善待过,张子静也是尽到了为人子的责任,对父亲和后母一一养老送终。
在张子静的回忆里,他重复地写到张爱玲去国离乡带给他的伤心:“一九五二年我调到浦东乡下教书。那时大家都忙着政治学习,我也较少回上海市区,和她见面的机会就少了。那年八月间,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区,急急忙忙到卡尔登公寓找她。姑姑开了门,一见是我就说:’你姐姐已经走了。’然后把门关上。我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都是穿人民装的人。我记起有一次她说这衣服太呆板,她是绝不穿的。或许因为这样,她走了。走到一个她追寻的远方,此生再没回来。”
在1980年代,张爱玲与在大陆的劫后余生的姑姑、弟弟通信。她给姑姑寄钱。在晚年张子静的笔下,他和姑姑虽然同住上海,却已经是半世未见,姑姑再婚和离世的消息,都是从报上得知的。值得一提的是。姑姑张茂渊在青年时期和黄逸梵一起远赴欧洲留学,曾经在远洋邮轮上邂逅一位上海前往欧洲读书的留学生李开第,归国后,双方一直是好朋友,李开第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张茂渊还是女方的伴娘,担任婚礼的傧相。李开第曾经在香港工作,张爱玲在香港大学读书时,李开第便担任她的监护人。风风雨雨半个世纪,李开第的原配病逝,他和张茂渊在文革中都九死一生,熬出一条命来,文革结束后,二人结婚,当时张茂渊已经78岁了。二人相守了十多年,先后过世。所有目睹过他们相处的人都说,这对夫妻是极为恩爱的,彼此珍惜,形影不离,张茂渊每天喝中药,都是先生为她熬好,亲自伺候她服下。
姑姑的故事,算是枯荣自守,按照她自己的脾性,走完了她的一生。
而弟弟呢,依然是张爱玲眼里那个混沌的弟弟。通信之后,弟弟照例伸手向她要钱,说自己退休了,打算找个伴一起安度晚年,想在上海买个房子一起过日子,张爱玲则回信抱歉地说自己能力不足,帮不上他。这样贵族世家的落魄子弟,改朝换代了他们的故事依然有自己的脉络,寻常的情节。男人们个个都在伸手要钱,一辈子都在伸手要钱。彼此礼节齐全的互相问候,一方伸手要钱,另一方则好声好气却斩钉截铁的回绝。张爱玲的精明,则和《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没什么两样,总之,要钱是没有的。论起烦难,她板着指头也能诉苦诸多。曹七巧带着黄金的枷锁劈死了好些人,将自己骨肉的一生可能的幸福全都耽误了。张爱玲笔下的家族至亲之间,也都牢牢地戴着这副黄金枷锁,谁都不曾卸下。手上的钱攥得紧紧的,手足亲情是为了张口借钱和防止被借钱而存在的一种关系。为了钱,兄妹之间可以打官司;为了钱,原告可以被被告收买,背叛手足,直到彼此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同样地,张爱玲对待她的弟弟,也不曾摆脱这个黄金枷锁。
在张子静曾是一个少年时,和他后来的生命晚期,都写过“我的姊姊张爱玲”这样的文章,晚年接受记者采访谈张爱玲。他很忠厚,回忆起父亲、母亲、姐姐,一律都有温暖底色。同样,他抱歉着自己这样平庸而寒苦的一生,实在是配不上那样才情飞扬的姐姐。然而,他以她为骄傲。
张爱玲过世的时候,身后不可谓不丰厚,她的银行账户里还有数万美金的存款和数十万美金的投资获利,她立遗嘱将身后事——财产和文字版权,全留给了香港文友宋淇夫妇。而这时候,她弟弟还活在上海,依然在窘迫孤苦之中。有追踪张爱玲上海行踪的港台张迷到上海,找到张爱玲的弟弟,印象里无一不是他的凄苦,种种窘迫。晚年的张子静好酒,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喝酒,那大概是他生活里唯一能慰藉他,也是唯一能麻醉他的感知的嗜好吧。他生活的那条街,都是老底子的上海人,许多近代史上的名流世家居住在此。有街坊日后为街坊邻居写忆旧文章,也提及到张爱玲的后母和弟弟。说的依然是张子静的潦倒和静默,和张爱玲一样,张子静也是不会做家务的。大雪天气里登门去街坊家,穿着一双有洞的单鞋子,站在人家门洞里,满地雪水。人家赶紧给他干净鞋子换上。可见这个孤身老人的生活凄惶情形。他也就这么潦倒到死。
而张爱玲的遗嘱委托人宋淇夫妇,本也都是高龄。他们相继过世后,其子宋以朗合法接管了这份遗嘱,成为委托人,他将张爱玲的遗稿翻了个底朝天,她生前决意不肯拿出来的稿子,全被其统统拿了出来,一一出版面世。一时舆情哗然。在《小团圆》里,我们获悉了张爱玲所有自爆家丑,在《异乡记》,我们读到了一个未完的伤心故事。然而,这一切,真的是张爱玲要的吗?是她委托给宋淇夫妇的真义吗?她自己不曾说出不曾出版的那些,真的是希望身后藉由他人之手,让残稿曝光吗?我们身为看客,大抵,也只是在这样的故事情节里,油然感叹一番世事人心的诡谲莫测吧。即使孤高如张爱玲,也不能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