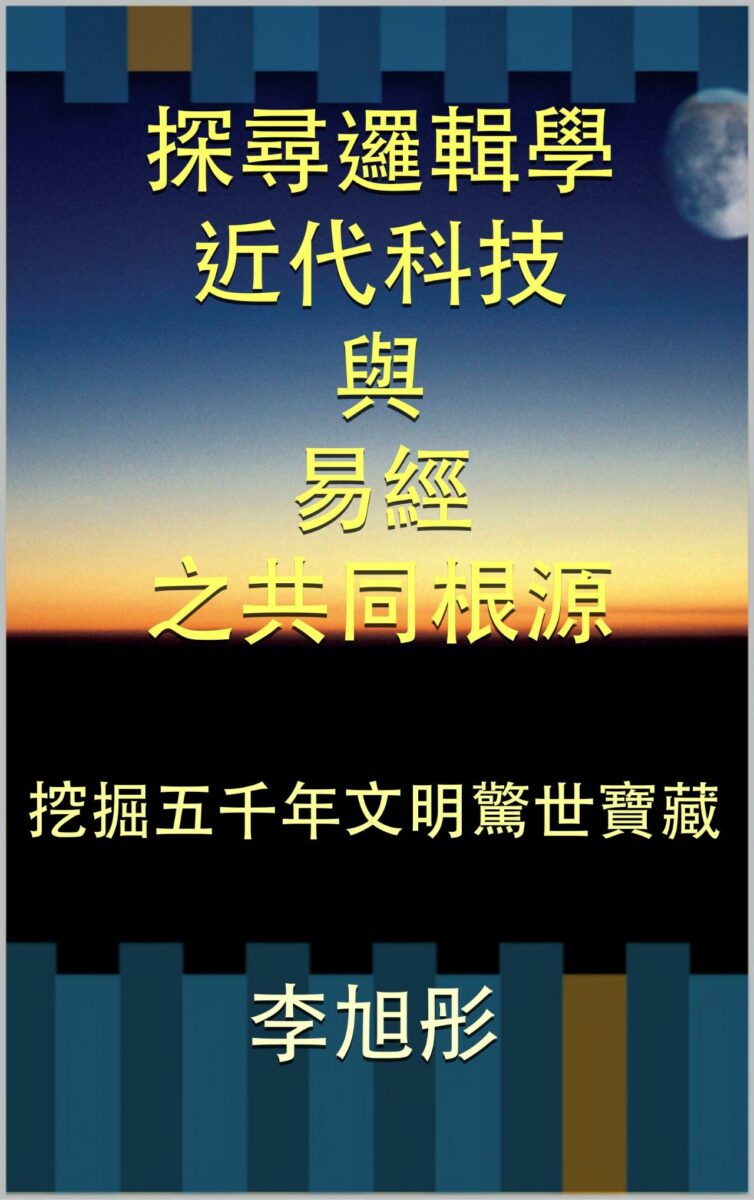【歐洲希望之聲原創】虽说名人效应巨大,影响深远,文人画迄今风头看似不减,却有愈来愈多有识之士重新审视它,并戳穿其遗祸。
苏东坡很敬重其表兄文同(北宋著名画家、诗人),他在墨竹上主要师从文同,但比文同更加简省。
苏东坡画竹,意在运用笔墨来表露他的真性情,正如他的侍妾朝云所说的,表露“一肚子不合时宜”。
苏东坡的论画格调:重视神似,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士夫画”,即文人画。反对院体重工整、精丽的风格,主张逸笔草草,不着力求工。这与两宋画院以纤丽浓艳和追求形似的主张完全背道而驰。他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他在这里明确强调要取其“意气”。“意”就是意兴、意趣、意境;“气”就是气概、气势、气韵。苏东坡的言行明示:他是主观地把工笔与写意彻底加以割裂。苏东坡曾经说过:“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之后的文人竟以此话来攻击画得似的画家。而在清代著名画家恽南田看来,“似”与“不似”都不是绘画的最高境界——“传神”。他说:“世人皆以不似为妙,余则不然,惟能极似,乃称与画传神。”其实,工笔画非常注重“意气”,且特别讲究色彩的运用,是更完美地在写意,其具足了表现力——形神兼备。
文人画基本上排斥色彩,通常以水墨为正宗,这种声言“运墨而五色”的单色画,与大写意的笔触、不求形似的所谓“造型”相结合,恰好迎合了无绘画基本功(造型能力、色彩感觉等)的文人们心绪的宣泄——一挥而就的放纵与满足。

由于苏东坡身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在世间影响力之巨大堪称无与伦比,此等中国文化史上极其少有的多才多艺的人物,再来几笔墨竹、奇石,自然就当之无愧的又添著名头衔——文人画创始人。明代大文豪、史学家、书法鉴定家王世贞曾说:“文人画起自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由于苏东坡极力倡导“文人画”,此头一开,一泻千里,尤其明清时代竟被夸张到了一切绘画原则均被其取而代之,使之成为社会心理病态甚至一种怪癖了。而文人画以水墨代替五色为最高境界,因此,排斥色彩艺术也就必然形成气候,就算还用点简单的色彩,也只是在完成的水墨画面上略施淡彩,仅此而已。此等理念之泛滥,特别是明清以来,从名家至附庸风雅者的绘画几乎都呈现出灰黑或灰黑间稍有淡彩的画面,死气沉沉,令人郁闷。这种无彩的缺憾直到晚清才被以海派画家任伯年、吴昌硕为代表的一批画家们敏感到,并设法为中国画找回失去已久的色彩。其努力仅局限于打点小补丁而已,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画江河日下的大局。究其原因,无非是受眼力与胆识等各种因素的限制,因而不识“色彩大师”的真面目——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汉唐艺术时代。


唐代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中的一个分水岭。之前的汉唐时代为当时全球最强盛富有的社会自不必说,与安史之乱后的宋元明清历朝对比,更是一个开放的、富有的、健康的时代。唐末五代以后,中国社会逐渐衰弱,人格也随之被扭曲。从艺术层面观之,且不说汉代的飘逸、雄壮、健康,只是唐代的壮硬、华丽、明快之风已让后人望洋兴叹。在绘画上,唐代简直就是一个色彩主义的时代,其五彩缤纷和色彩流动之美,是其后千余年间的艺术所不可企及的。可悲的是,自北宋文人画的理论开始流行以后,文人以无拘无束的水墨游戏为正宗,唐以前的画风竟被斥为工匠之作,谓之格调不高,这其实是以少数文人的喜好来代替整个绘画艺术的审美原则,其影响深远,祸乱无穷。面对如此颓败景象,迫切需要有识之士担当重任——发掘传统文化瑰宝,弘扬传统的中国绘画艺术。

还好,此时出了个张大千,他以独具的历史慧眼和以古开今的超凡艺术功力,把找回中国画色彩的路径直指史上最辉煌的汉唐艺术时代,此举可谓坦途、正道、精准无误。在张大千的勤奋努力和影响下,于非闇、谢稚柳、晏济元诸人挖掘出许多古人常用而文人画基本不用的色彩及复杂用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大千不是理论家,也乏理论著述,可他却是一位罕见的、特有胆识的全才型(山水、人物、花鸟、动物各科皆精)艺术家,而且最过人之处在于他具有超绝的眼力,识得汉唐绘画艺术珍宝,不被近千年的所谓文人画所迷蒙,因此,对传统绘画的发掘和整理不遗余力,不计同行非议,以中国画艺术传统中最通行的临摹方式来进行,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可遗憾的是,张大千目疾之后,曾一度变为极抽象的纯水墨,然后又泼墨泼彩,尽管他最后又回到具象的制作,但那一时期的作品毕竟在中国画界造成了很大负面影响,以至于现在仍有人奉为圭臬。

虽说名人效应巨大,影响深远,文人画迄今风头看似不减,却有愈来愈多有识之士重新审视它,并戳穿其遗祸。
部分宋代近代畫作:




責任編輯:李文涵
(轉載請註明歐洲希望之聲,並包括原文標題及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