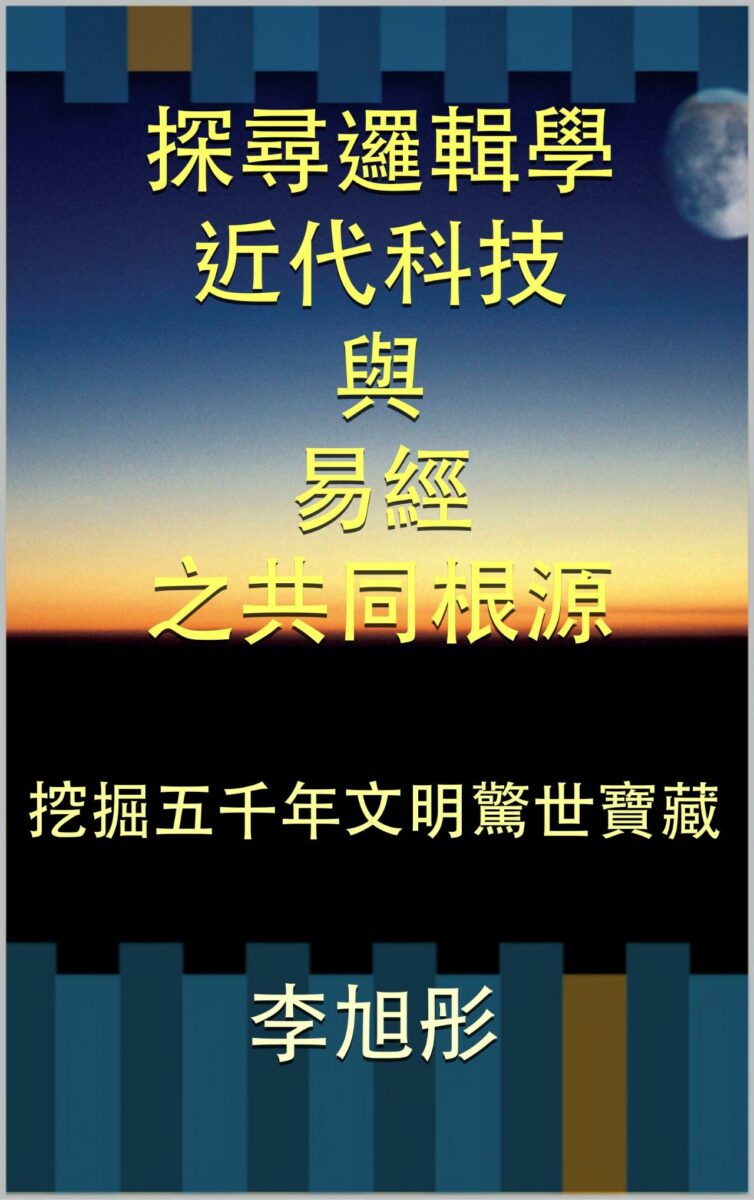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致病是因为鼠疫杆菌,死亡率极高,目前为止死亡总数高达2亿人,肆虐地球至少300年。
历史上鼠疫有三次大流行,首次大流行发生于六世纪,起源于埃及的西奈半岛,波及到欧洲所有国家,死亡近二千五百万人。但由于缺乏详细资料确认,一般不能确认这是鼠疫造成的。
第二次发生于十四世纪,仅欧洲就死亡二千五百万人,即历史上著名的黑死病,英国近1/3的人口死于鼠疫。到1665年,这场鼠疫肆虐了整个欧洲,几近疯狂。仅伦敦地区,就死亡六七万人以上。1665年的6月至8月的仅仅3个月内,伦敦的人口就减少了十分之一。到1665年8月,每周死亡达2000人,9月竟达8000人。鼠疫由伦敦向外蔓延,英国王室逃出伦敦,市内的富人也携家带口匆匆出逃,剑桥居民纷纷用马车装载着行李,疏散到了乡间。伦敦城有1万余所房屋被遗弃,有的用松木板把门窗钉死,有病人的住房都用红粉笔打上十字标记。当时还是大学生的牛顿,还因此从英国剑桥大学辍学一阵子。
据说最初黑死病从中亚地区向西扩散,并在1346年出现在黑海地区。它同时向西南方向传播到地中海,然后就在北太平洋沿岸流行,并传至波罗的海。约在1348年,黑死病在西班牙流行,到了1349年,就已经传到英国和爱尔兰,1351年到瑞典,1353年到波罗的海地区的国家和俄罗斯,连莫斯科大公和东正教的教主都相继死去。黑死病的魔爪伸向了各个社会阶层,没有人能逃避死亡的现实。
只有路途遥远和人口疏落的地区才未受伤害。根据今天的估算,当时在欧洲、中东、北非和印度地区,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的人口因而死亡。
西方一般把这次作为鼠疫爆发的首次记录。
第三次发生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死亡一千二百万人。
传说黑死病起源于亚洲西南部,一说起源于黑海城市卡法,约在1340年代散布到整个欧洲,而“黑死病”之名是当时欧洲的称呼。这场瘟疫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约7500万人死亡,而当时世界人口只有三到四亿人,其中明朝人口就有六千多万。
同样的疾病多次侵袭欧洲,直到1700年代为止,期间造成的死亡情形与严重程度各不相同。较晚的几次大流行包括1629年到1631年的意大利瘟疫、1665年到1666年的伦敦大瘟疫、1679年的维也纳大瘟疫、1720年到1722年的马赛大瘟疫,以及1771年的莫斯科瘟疫。关于这些疾病的异同仍有争议,但是其致命型态似乎于18世纪消失于欧洲。
黑死病对于欧洲的历史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黑死病对欧洲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动摇了当时支配欧洲的罗马天主教会的地位,并因此使得一些少数族群受到迫害,例如犹太人、穆斯林、外国人、乞丐以及痳疯病患。生存与否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产生了“活在当下”的一种情绪,如同薄伽丘在《十日谈》之中所描绘的一般。

14世纪发生于欧洲的事件,刚开始被当时的作家称作“Great Mortality”,瘟疫爆发之后,又有了“黑死病”之名。一般认为这个名称是取自其中一个显著的症状,称作“acral necrosis”,患者的皮肤会因为皮下出血而变黑。而黑色实际上也象征忧郁、哀伤与恐惧。
黑死病的病原体现在可能已经灭绝。
现在大家自然都知道,黑死病是一种鼠疫,是通过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但当时没有人知道致病的原因,所以也无法预防。
最大规模的一场黑死病,应该是14世纪初期。
1348年,一场鼠疫大流行,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进程,也改变了人类的卫生保健史。这个时候是中国的元朝末年。
这次鼠疫最早由一位名叫博卡奇奥的意大利佛罗伦萨人记录下来:最初症状是腹股沟或腋下的淋巴有肿块,然后皮肤会出现青黑色的斑块,因此当时被称为黑死病。染病后,几乎所有的患者都会在3天内死去。
疫病皆有传染源,黑死病的源头是老鼠及其携带的跳蚤。当时传说:最早感染黑死病的是蒙古人。蒙古人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草原上的老鼠把瘟疫传染给了他们。蒙古人居于中国北方,从成吉思汗起向西扩张,横扫中亚和欧洲。
鼠疫于1331年开始肆虐中国。时值中国住民武力反抗元朝统治的顶点,元朝遂于1368年灭亡于明朝。其实在元朝之前,鼠疫曾多次传入中国,所以虽然中国也曾发生过地区性鼠疫传染,但中国人也逐渐有了对鼠疫的免疫力,死亡率相对较低。而欧洲人则在此之前几百年内从未接触过鼠疫,一旦爆发,自然死亡惊人。
1345年,占领中亚、西亚的蒙古人进攻黑海之滨一个叫加法的城邦,加法向东罗马帝国称臣。面对骁勇善战的蒙古人,加法人坚壁清野,闭城不战。蒙古人围城一年,久攻不下,而瘟疫在蒙古大军中蔓延。蒙古人知道这种瘟疫会传染,于是用抛石机将染病身亡的士兵的尸体抛入城内,这可谓全世界最早的细菌战。加法人不了解这种瘟疫,对抛进来的尸体置之不理,甚至莫名其妙。尸体腐烂后,恐怖的瘟疫便随之爆发。现在看来,是腐烂的尸体释放出病菌,污染了空气,毒化了水源,导致了瘟疫。
加法人大批死亡,全城恐怖,打开城门,纷纷仓皇逃窜。而城外的蒙古大军也没有高兴多久。入城几天后,他们同样放弃加法仓皇逃走,因为鼠疫也没有放过他们,蒙古人也大量死于黑死病。
劫后余生的加法人乘船逃往他们的宗主国——东罗马帝国。然而,加法城爆发瘟疫的消息已经传遍欧洲,所有的港口都拒绝他们登陆。意大利威尼斯让他们的船只在海上隔离40天后才准许上岸,意在阻止瘟疫传入。
只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船上携带细菌的老鼠却会游泳,它们早已泅渡到岸上,可怕的黑死病因此开始在整个欧洲蔓延。
当时欧洲城市的卫生极差,大街上四溢着脏水和粪便,到处都是垃圾和杂物,这正是老鼠的天堂。任何一个欧洲城市,都有大量的老鼠存在。
欧洲人把瘟疫的爆发迁怒于人,首当其冲的就是犹太人。
在德国的梅因兹,有1.2万犹太人被当作瘟疫的传播者被活活烧死,斯特拉堡则有1.6万犹太人被杀。只有少数头脑清醒的人意识到可能是动物传播疾病,于是他们把仇恨的目光集中到猫狗等家畜身上,他们杀死所有的家畜,大街上满是猫狗腐败的死尸,腐臭的气味让人窒息,不时有一只慌乱的家猫从死尸上跳过,身后一群用布裹着口鼻的人正提着木棍穷追不舍。没有人会怜悯这些弱小的生灵,因为它们被当作瘟疫的传播者。
当时,欧洲教会不知道老鼠是传染源,认为猫是幽灵和邪恶的化身,鼓动人们捕杀猫。猫几乎濒临灭绝。加上瘟疫爆发后,人们认为猫有可能是传播瘟疫的载体,更是大肆捕杀。没有了天敌的老鼠肆意繁殖,加剧了黑死病的流行。那时欧洲的医学也非常落后,不论得了什么病,都是千篇一律地实行放血疗法,放血不奏效,又使用通便剂、催吐剂,仍不奏效,就用火烧灼淋巴肿块。
这都是西方医学鼻祖、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传下来的方法,不过也超越了希波克拉底,新疗法是把干蛤蟆放在皮肤上,或者用尿洗澡。这些疗法自然也无效。于是人们只好相信上帝,把瘟疫归结为人类自身的罪孽惹得上帝愤怒。要赎罪,一些人手执带着铁尖的鞭子彼此鞭打,一边被打一边哼唱着“我有罪”。
这场黑死病使欧洲人死亡约2500万,占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所造成的恐怖只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才可比拟。
古代欧洲人对于这次黑死病的恐惧,胜过对战争的恐惧。意大利人薄伽丘的《十日谈》写作背景就是黑死病流行时期。当时佛罗伦萨十室九空,七位男青年和三位姑娘为避难躲到郊外的一座别墅中。为消耗时间,他们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一共讲了十天,讲了一百个故事。《十日谈》书名由此而来。
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写道:在我主降生后第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的城市中最美丽的城市——就是那繁华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怖的瘟疫。这场瘟疫不知道是受了天体的影响,还是威严的天主降于作恶多端的人类的惩罚;它最初发生在东方,不到几年工夫,死去的人已不计其数;而且眼看这场瘟疫不断地一处处蔓延开去,后来竟不幸传播到了西方。大家都束手无策,一点防止的办法也拿不出来。城里各处污秽的地方都派人扫除过了,禁止病人进城的命令已经发布了,保护健康的种种措施也执行了;此外,虔诚的人们有时成群结队、有时零零落落地向天主一再作过祈祷了;可是到了那一年的初春,奇特而可怖的病症终于出现了,灾难的情况立刻严重起来。
这里的瘟疫,不像东方的瘟疫那样,病人鼻孔里一出鲜血,就必死无疑,却另有一种征兆。染病的男女,最初在鼠蹊间或是在胳肢窝下隆然肿起一个瘤来,到后来愈长愈大,就有一个小小的苹果,或是一个鸡蛋那样大小。一般人管这瘤叫“疫瘤”,不消多少时候,这死兆般的“疫瘤”就由那两个部分蔓延到人体各部分。这以后,病征又变了,病人的臂部、腿部,以至身体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现了黑斑或是紫斑,有时候是稀稀疏疏的几大块,有时候又细又密;不过反正这都跟初期的毒瘤一样,是死亡的预兆。
任你怎样请医服药,这病总是没救的。也许这根本是一种不治之症,也许是由于医师学识浅薄,找不出真正的病源,因而也就拿不出适当的治疗方法来——当时许许多多对于医道一无所知的男女,也居然像受过训练的医师一样,行起医来了。总而言之,凡是得了这种病、侥幸治愈的人,真是极少极少,大多数病人都在出现“疫瘤”的三天以内就送了命;而且多半都没有什么发烧或是其他的症状。
这瘟病太可怕了,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仿佛干柴靠近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不,情况还要严重呢,不要说走近病人,跟病人谈话,会招来致死的病症,甚至只要接触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摸过的东西,也立即会染上了病。
活着的人们,每天看到这一类或大或小的惨事,心里就充满着恐怖和种种怪念头;到后来,几乎无论哪一个人都采取了冷酷无情的手段:凡是病人和病人用过的东西,一概避不接触,他们以为这样一来,自己的安全就可以保住了。
有些人以为唯有清心寡欲,过著有节制的生活,才能逃过这一场瘟疫。于是他们各自结了几个伴儿,拣些没有病人的洁净的宅子住下,完全和外界隔绝起来。他们吃着最精致的食品,喝着最美的酒,但总是尽力节制,绝不肯有一点儿过量。对外界的疾病和死亡的情形他们完全不闻不问,只是借音乐和其他的玩意儿来消磨时光。
也有些人的想法恰巧相反,以为唯有纵情欢乐、纵饮狂歌,尽量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什么都一笑置之,才是对付瘟疫的有效办法。他们当真照着他们所说的话实行起来,往往日以继夜地,尽情纵饮,从这家酒店逛到那家酒店,甚至一时兴来,任意闯进人家住宅,为所欲为。也没有人来阻拦他们,因为大家都是活了今天保不住明天,哪儿还顾得到什么财产不财产呢。所以大多数的住宅竟成了公共财产,哪一个过路人都可以大模大样地闯进去,只当是自己的家一般占用着。可是,尽管他们这样横冲直撞,对于病人还是避之唯恐不及。
浩劫当前,这城里的法纪和圣规几乎全都荡然无存了;因为神父和执法的官员,也不能例外,都死的死了,病的病了,要不就是连一个手底下人也没有,无从执行他们的职务了;因此,简直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
还有好多人又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态度。他们既不像第一种人那样严格节制着自己的饮食,也不像第二种人那样大吃大喝、放荡不羁。他们虽然也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适可而止,他们并没有闭户不出,也到外面去走走,只不过手里总要拿些什么鲜花香草,或是香料之类,不时放到鼻子前去嗅一下,清一清神,认为要这样才能消除那充满在空气里的病人、药物和尸体的气味。
有些人为了自身的安全,竟抱着一种更残忍的见解。说,要对抗瘟疫,只有一个办法——唯一的好办法,那就是躲开瘟疫。有了这种想法的男男女女,就只关心他们自己,其余的一概不管。他们背离自己的城市,丢下了自己的老家,自己的亲人和财产,逃到别的地方去——至少也逃到佛罗伦萨的郊外去,仿佛是天主鉴于人类为非作歹,一怒之下降下惩罚,这惩罚却只落在那些留居城里的人的头上,只要一走出城,就逃出了这场灾难似的。或者说,他们以为留住在城里的人们末日已到,不久就要全数灭亡了。
这些人的见解各有不同,却并没个个都死,也并没全都逃出了这场浩劫。各地都有好些各色各样的人在自身健康时,首先立下榜样,教人别去理会那得病的人,后来自己病倒了,也遭受人们的遗弃,没人看顾,就这样断了气。
真的,到后来大家你回避我,我回避你;街坊邻舍,谁都不管谁的事了,亲戚朋友几乎断绝了往来,即使难得说句话,也离得远远的。这还不算,这场瘟疫使得人心惶惶,竟至于哥哥舍弃弟弟,叔伯舍弃侄儿,姊妹舍弃兄弟,甚至妻子舍弃丈夫都是常有的事。最伤心、叫人最难以置信的,是连父母都不肯看顾自己的子女,好像这子女并非他们自己生下来似的。
因此许许多多病倒的男女都没人看顾,偶然也有几个朋友,出于慈悲心,来给他们一些安慰。不过这是极少数的;偶然也有些仆人贪图高额的工资,肯来服侍病人,但也很少很少,而且多半是些粗鲁无知的男女,并不懂得看护,只会替病人传递茶水等物,此外就只会眼看着病人死亡了。这些侍候病人的仆人,多半因此丧失了生命,枉自赚了那么些钱。
就因为一旦染了病,再也得不到邻舍亲友的看顾,仆人又这样难雇,就发生了一种闻所未闻的风气。那些太太小姐,不管本来怎么如花似玉,怎么尊贵,一旦病倒了,她就再也不计较雇用一个男子做贴身的仆人,也再不问他年老年少,都毫不在乎地解开衣裙,把什么地方都在他面前裸露出来,只当他是一个女仆。她们这样做也是迫于病情,无可奈何,后来有些女人保全了性命的,品性就变得不那么端庄,这也许是一个原因吧。
有许多病人,假如能得到好好的调理,本来可以得救,现在却都死去了。瘟疫的来势既然这么凶猛,病人又缺乏护理,叫呼不应,所以城里日日夜夜都要死去大批大批的人,那情景听着都叫人目瞪口呆,别说是当场看到了。至于那些幸而活着的人,迫于这样的情势,把许多古老的习俗都给改变过来了。
照向来的风俗说来(现在也还可以看到),人死了,亲友邻居家的女眷都得聚集在丧事人家,向死者的家属吊唁;那家的男子们就和邻居以及别处来的市民齐集在门口。随后神父来到,人数或多或少,要看那家的排场而定。棺材由死者的朋友抬着,大家点了一支蜡烛,拿在手里,还唱着挽歌,一路非常热闹,直抬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但是由于瘟疫越来越猖獗,这习俗就算没有完全废除,也差不多近于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风气。病人死了,不但没有女人们围绕着啜泣,往往就连断气的一刹那都没有一个人在场。真是难得有几个死者能得到亲属的哀伤和热泪,亲友们才不来哀悼呢——他们正在及时行乐,在欢宴,在互相戏谑呢。女人本是富于同情心的,可是现在为了要保全自己的生命,竟不惜违背了她们的本性,跟着这种风气走。
再说,人死了很少会有十个邻居来送葬;而来送葬的决不是什么有名望有地位的市民,却是些低三下四的人——他们自称是掘墓者;其实他们干这行当,完全是为了金钱,所以总是一抬起了尸架,匆匆忙忙就走,并不是送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而往往送到最近的教堂就算完事。在他们前面走着五六个僧侣,手里有时还拿着几支蜡烛,有时一支都不拿。只要看到是空的墓穴,他们就叫掘墓人把死尸扔进去,再也不自找麻烦,郑重其事地替死者举行什么落葬的仪式了。
下层阶级,以至大部分的中层阶级,情形就更惨了。他们因为没有钱,也许因为存着侥幸的心理,多半留在家里,结果病倒的每天数以千计。又因为他们缺乏适当的医治,无人看护,几乎全都死了。白天也好,黑夜也好,总是有许多人倒毙在路上。许多人死在家里,直到尸体腐烂,发出了臭味,邻居们才知道他已经死了。
城市里就这样到处尸体纵横,附近活着的人要是找得到脚夫,就叫脚夫帮着把尸体抬出去,放在大门口;找不到脚夫,就自己动手,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恻隐之心,而是唯恐腐烂的尸体威胁他们的生存。每天一到天亮,只见家家户户的门口都堆满了尸体。这些尸体又被放上尸架,抬了出去,要是弄不到尸架,就用木板来抬。
一个尸架上常常载着两三具尸体。夫妻俩,或者父子俩,或者两三个兄弟合放在一个尸架上,成了一件很普通的事。人们也不知道有多少回看到两个神父,拿着一个十字架走在头里,脚夫们抬着三四个尸架,在后面跟着。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神父只道要替一个人举行葬礼,却忽然来了六七具尸体,同时下葬,有时候甚至还不止这么些呢。再也没有人为死者掉泪,点起蜡烛给他送丧了;那时候死了一个人,就像现在死了一只山羊,不算一回事。本来呢,一个有智慧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偶尔遭遇到几件不如意的事,也很难学到忍耐的功夫;而现在,经过了这场空前的浩劫,显然连最没有教养的人,对一切事情也都处之泰然了。
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尸体运到全市的教堂去,教堂的坟地再也容纳不下了,尤其是有些人家,按照习俗,要求葬在祖坟里面,情形更加严重。等坟地全葬满了,只好在周围掘一些又长又阔的深坑,把后来的尸体几百个几百个葬下去。就像堆积船舱里的货物一样,这些尸体,给层层叠叠地放在坑里。只盖着一层薄薄的泥土,直到整个坑都装满了,方才用土封起来。
最后意大利人(其实当时还没有意大利这个国家)无意中,找到了一种阻挡瘟疫蔓延的有效办法:隔离。当瘟疫快要蔓延到米兰时,大主教下令,对最先发现瘟疫的三所房屋进行隔离,在周围建起围墙,围墙内的所有人不许迈出半步,结果米兰避免了瘟疫。这是人类对传染病第一次建立隔离制度,并一直沿用至今。
黑死病在客观上促进了医学的进步。一个名叫希利亚克的医生在教皇支持下开始解剖死者的尸体,而在此之前解剖尸体被教会视为大逆不道,必须坐牢甚至处死。希利亚克正确判断出鼠疫的两种类型,即肺鼠疫和淋巴腺鼠疫,前者通过空气传播,后者通过血液传播,前者的感染性更强。解剖学由此开始发展,西方医学逐渐认识了人体生理,进而促进了外科学的发展。
欧洲人为了保命,也被迫改善了卫生习惯。在此之前,在巴黎、罗马、佛罗伦萨等城市的街道上,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人们终年不洗一次澡,为遮掩体味,法国人才发明了香水。鼠疫流行后,欧洲各国积极加强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如挖掘宽敞的下水道,并且重视对垃圾的处理,加上普遍进行杀虫和消毒,使鼠疫等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因此,国际上把对鼠疫的防治称为“第一次卫生革命”。
从14世纪一直到17世纪中叶,黑死病每隔几十年都会在欧洲重现,但再也没有造成像第一次爆发时那样惨烈的疫情,这应归功于公共卫生的改善。到20世纪中叶,抗菌素的发明使鼠疫成了容易治愈的疾病,如今鼠疫仅在非洲贫穷落后地区偶尔发生。
欧洲鼠疫流行使人口大量死亡,劳动力极其短缺。瘟疫氾滥地区,无人看管的牛群羊群四处乱跑,牧羊人早已死去。因为工人和农民数量奇缺,农奴地位因此提高。
黑死病登陆英国土地的同一年,所有牲畜的价格都急剧下降,即便活着的人也很少能保住自己的财产。本来值40先令的一匹马,现在只能卖6.5先令,一头壮实的公牛只能卖4先令,一头母牛12便士,小牛6便士,一头羊3便士,一头肥猪5便士。羊群和牛群在田野里四处漫游,没人去照管它们,听凭它们死在农田里、沟渠里。
到了第二年的秋天,一个收割者替人干活索取的报酬大大提高了,每天不得低于8便士。还得供他吃饭。许多庄稼在田里腐烂掉了,因为请不起人来收割它们。在瘟疫流行的年代,劳动力的匮乏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时,英国国王发布命令说,无论是收割庄稼的工人还是其他雇工,都不准索取高于往年水平的工资,违反者将给予严厉惩罚。但是劳工们根本不理睬国王的命令。任何人想要雇佣他们,都得付出比往年多得多的钱,否则就让你的庄稼或者果实腐烂在农田和果园里。
在英格兰瘟疫肆虐时,苏格兰人也跑来趁火打劫。当他们听说英格兰人中间正在流行着瘟疫时,以为他们的诅咒终于应验了,因为他们一直在诅咒:“让该死的英格兰人都在瘟疫中死去吧。”现在一定是上帝在惩罚英格兰人了。于是,苏格兰人在塞尔克森林聚集起来,准备协助上帝彻底的消灭英格兰人。但这个时候,黑死病也传到了苏格兰,在几天的时间里就死了5000个苏格兰人。剩下的人准备返回自己的家园,却遭到英格兰人的反击,死伤又过大半。
鼠疫造成的劳动力奇缺,导致底层民众要求更多的权利和自由,欧洲封建贵族由此开始逐步衰落,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步走上历史舞台,直至出现资产阶级革命。一场传染病,就这样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而英国的鼠疫更有戏剧性,1666年9月10日,伦敦布丁巷内一家面包店发生火灾。当时伦敦非常干燥,加上伦敦以木质建筑为主,火势迅速蔓延到了整个城市,连烧了三天三夜,第四天被扑灭,造成4/5市区被毁,包括87间教堂、44家公司以及13000多间民房。奇特的是,此后人类百战不胜的鼠疫竟然彻底从英国消失了。
作者: 萨沙
转自:看中国
责任编辑:美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