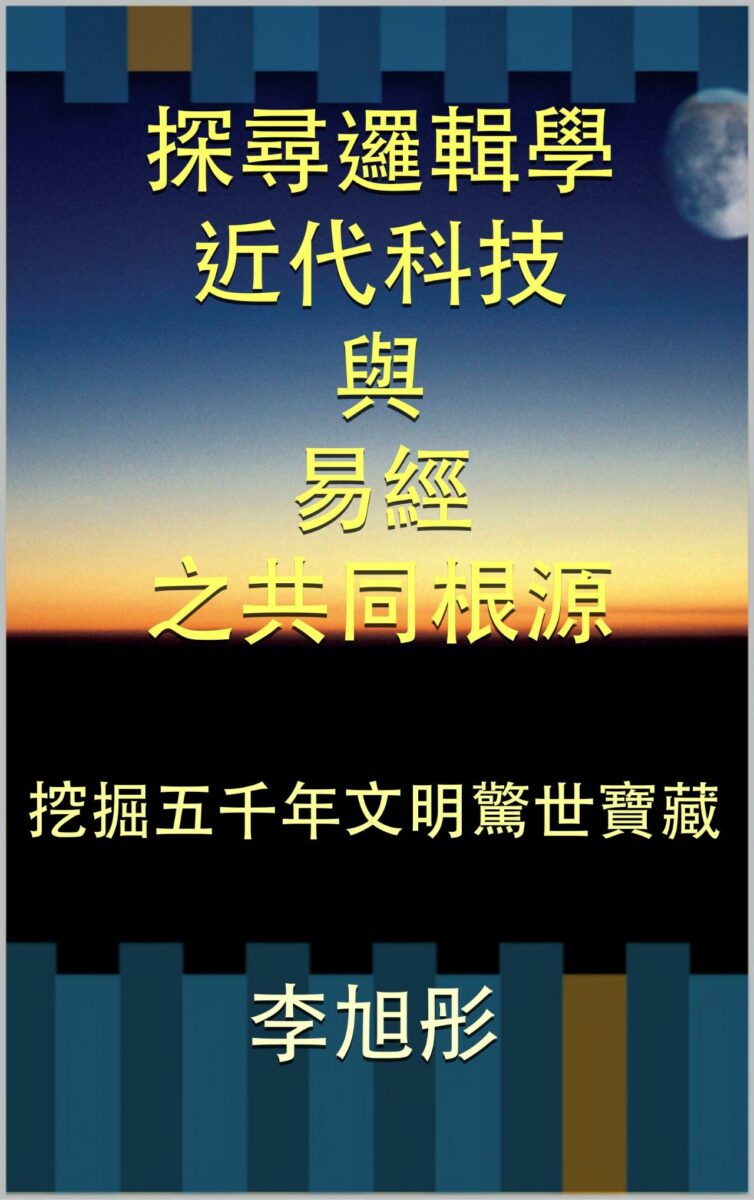穆增蕊和父亲、母亲不停地遭到一批又一批红卫兵的毒打。图为文革批斗场面,与本文主人公无关。(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穆增蕊和父亲、母亲不停地遭到一批又一批红卫兵的毒打。图为文革批斗场面,与本文主人公无关。(图片来源:网络图片)她的父亲是被她亲手杀死的。
那天,在父亲和母亲的一致哀求下,最终三个人商量好,由她亲手为他们割断颈动脉。
这是最快捷的一种死亡方式,结束生命仅需一分钟。
她是个医生,这对她来说,很简单。
她叫穆增蕊。
那天,是1966年8月29日凌晨。
穆增蕊,高中毕业于天津市女七中。女七中的前身是天津著名的私立中学——南开女中。1952年私立学校被取消,南开女中改为公立学校,名为天津市女七中。
穆增蕊所在的班级是女七中那一届唯一的一个高中班。她是我姐姐的同班同学。她的同学们都记得,她原来是一个文静、谦虚、乐观向上、待人诚恳、品学兼优的女孩。
高中毕业,她考取了医学院。大学毕业,分配到天津市儿童医院工作。她在医院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广受患者爱戴。文革前,曾被评为医院的先进工作者。婚后的穆增蕊,丈夫在北京工作,两个人分居两地,为了工作,她甚至将第一次怀上的孩子做了流产,以后就再也没能怀上孕。
1949年以前,穆家是开茶庄的。穆家茶庄的茉莉花茶在天津卖出了名气。相声大师马三立的相声《起名字的艺术》有这样的内容:“哪儿买茶叶?正兴德……这字儿让你容易记住,叫着还顺嘴儿。”“正兴德”就是穆家茶庄的名号,在老天津可以说几乎人人皆知。
当然,自从1956年实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正兴德茶庄早就“公私合营”归了共产党了,穆家也早已不做买卖了。祖上的家产唯独就剩下了一栋三层小楼。穆增蕊的父母住在二楼,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住在一楼,一楼还有一间屋子对外出租。这一间屋子的租金就成了她父母唯一的收入和生活来源。
1964~1965年,穆增蕊参加农村巡回医疗队下乡服务,工作过劳加上生活条件艰苦,后来一下子病倒了。66年返回市里以后她就回了娘家,住到了父母处。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开始。社论宣称:“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我国,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国解放16年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是要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最彻底的革命,这不能不遇到剥削阶级最顽强的反抗。”
8月26日一大早,一群中学生红卫兵手持皮带、大棒,砸开院门,冲进院里,开展革命行动。一部分红卫兵进屋抄家,另一部分就对住户施虐。他们先把穆增蕊和她父母三人的头发剃成阴阳头,用剪刀把裤子剪得稀巴烂,接着将人捆绑着拉到胡同口罚跪,进行批斗,批斗中拳脚相加,配合着皮鞭、木棒抽打,往身上、脸上刷墨汁、刷浆糊,百般凌辱,要他们承认是从事剥削、妄图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资本家。
穆增蕊很不理解。实际上,穆家从穆增蕊的父亲开始就没从事商业,她的父亲过去是个画家,穆家那时候既没有工厂、作坊,也没有公司、商店,从何而来的“剥削”?红卫兵蛮横地说,一楼出租一间屋就是剥削,就是不劳而获,就是阴谋复辟。
抄家从楼下抄到楼上,一层楼一层楼、一间屋一间屋刮地三尺般地进行:凡是能够打碎的全部打碎,凡是能够烧毁的全部烧毁、凡是能够拿走的全部拿走。他们疯狂地打砸,把一切物品砸了个稀巴烂,连饭碗都没有留一个;书、画全部堆到院子里付之一炬;其他物品,全部贴上封条,等待用车拉走。
抄家中,红卫兵们发现了穆增蕊的父亲过去在美国举办画展的一份资料,如获至宝,这可是里通外国的铁证,于是殴打、凌辱升级。从清早到晚上9、10点钟,穆增蕊和父亲、母亲不停地遭到一批又一批红卫兵的毒打,不许休息、没有水喝、没有进食,每天从早到晚,几乎没有间歇地遭受折磨:揪头发、扇耳光、用皮带抽,用木棒打,边被打还要边高喊“我有罪”、“我阴谋复辟,罪该万死”。一批红卫兵打累了就撤,又来一批继续,又是一番鞭打、凌辱。仅剩下半边头的头发被一绺绺地薅下来,脸颊被抽肿了,牙齿被打松动了、断裂了,嘴角、眼角流着血,膝盖跪破了,露出血淋淋的肉,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几乎体无完肤……这种折磨整整进行了三天。
三天里,大人粒米未进,只给她哥哥的孩子煮了一点点挂面。屋子里陡然间变得家徒四壁、一无所有,所有的东西要么被砸碎、砸烂,要么被撕碎、烧毁,要么被贴上封条等待拉走。电线被剪断,说是防止他们自杀。夜里没有灯,怕红卫兵随时闯进来,不敢躺下,更难以入眠,每晚摸黑坐等天亮,胆战心惊地等待第二天再次开始的凌辱、批斗和毒打。
第三天,8月28日,又是从清早到黑夜不停地罚跪、鞭打。28日夜里,穆增蕊依旧和父母在黑暗中席地对坐,又是整整一夜坐到凌晨。他们再也没有力气坐下去和跪下去了,也更经不住新的一天即将开始的毒打和批斗了。
“阿蕊啊,妈熬不住了!”先是妈妈轻轻地发出了颤抖的声音。
穆增蕊抱住了衰弱得稍微一碰就会倒下的妈妈的瘦削的身体,可是却一句劝解的话也说不出来。她能说什么呢?她没法鼓励妈妈挺住,也更不能对妈妈说她能够保护父亲、母亲,连她自己也挺不住了啊!
爸爸在依稀可辨的朦胧中下了决心,说:“阿蕊,你帮我和你妈解脱吧!只有这一个办法了。你是医生,你知道怎么搞能快一点。”
这个世界没有他们的活路,他们无处可逃,无处可藏,唯一的选择是离开这个世界、了结自己的生命。绝望中,他们想到的唯一解除痛苦的办法只有死亡。
穆增蕊说:“爹,妈,我和你俩一块去!”
于是,三个人就开始商量如何自杀。
熹微的曙光中,他们看到凌乱不堪的房间地板上,红卫兵落下的一串钥匙上有一把小小的水果刀。对于作为医生的穆增蕊来说,这就够了。她告诉父亲、母亲,她可以用这把水果刀先割断他们的颈动脉,然后再自割。这种办法走得快,一分钟就可以结束生命。
家里只有她是医生,也只有她才能准确、快速地找准、割准颈动脉,所以,给父亲、母亲割颈自然只能由她来操刀。而究竟先割爹还是先割妈,父亲、母亲两人却互相争执起来。因为先走可以先解脱痛苦,还有后走的为其送行,也不会感受眼看亲人死亡的痛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父母双方互相都想把优先条件让给对方。这也算是这个即将解体的家庭最后的一次温馨和亲情的体现吧!这也是他们最后能为亲人表达的一点心意吧!
最后决定,还是让父亲优先。于是,父亲也就最后一次享受了一把作为一家之主的“特权”——先被女儿割颈。由于商讨和争执,耽误了一些时间。当穆增蕊给父亲割开血管,天色已经放亮了。眼看着鲜红的血水猛的从颈部喷射出来,父亲还担心地问她,成功了吗?还有脉搏吗?穆增蕊满手、满身都是父亲颈部喷溅出来的鲜血。她勉强还来得及在父亲停止心跳、失去意识之前告诉父亲:放心,一分钟就会结束。
她转过身,正要给母亲割颈,就听到她的二哥慌慌张张跑上楼说,听到大门口有红卫兵来了。她浑身猛地一震,简直想死都不容易啊!连两个人两分钟的寻死的时间都不能获得啊!眼看给母亲和自己割颈已经来不及了,容不得穆增蕊多想,离开尘世、去往没有屈辱和痛苦的阴间是她当前唯一能做出的决定,越快越好。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撞开房门,快步跑上三楼,推开窗户,迅猛地朝楼下纵身一跃!……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醒来了,发现自己已在医院的病房里,她的左腿小腿胫骨骨折,右腿大腿骨横断骨折,面前还坐着两个一脸严肃的审讯人员。她不得不躺在病床上接受审讯。或许是为了稳定她的情绪以便她交代问题,审讯人员告诉她,她妈妈跟着她跳楼,是他们救过来的。这时她才知道,原来她母亲也跳了楼,并且以为母亲还活着。这期间,她的嫂子来医院看过她,告诉她是哥嫂把她和母亲抬到了医院。在医院以及后来在监狱中,哥嫂和侄儿看望他时,一直都没有告诉她母亲真实的消息。
在她给父亲割颈并跳楼9天以后,也就是1966年9月7日,她被宣布逮捕,在病床上被拷上了手铐。医院不再给犯人治疗,并要和她划清界限,她被立即押送到监狱医院。到了监狱医院,原来医院的人员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卸下腿骨的牵引带走。于是断骨又重新断裂,骨茬叉开。中午11点到达监狱医院,医务人员午休,直到下午两点才接受治疗。又重新穿钢针,重新拉牵引,一次又一次,放下,又拉,又放下又拉。一次次的放和拉,她居然不知道疼。但是,最终断骨也没有对准,她的右腿最后只有五分之一连合,成为了终生的残疾。
到了1968年,法院实行军管后,穆增蕊的案子被定性为“抗拒运动杀人罪”。杀人属于刑事罪,抗拒运动属于政治罪,比杀人罪更严重,数罪并罚,最终她被判处无期徒刑。
判决书内容如下:
查被告穆增蕊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解放后未得到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竟胆敢积极出谋划策,以自杀来抗拒运动,并亲自动手将XXX杀死,后又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甘愿与人民为敌,已构成抗拒运动杀人罪。性质严重,情节恶劣,证据确凿。本院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特判决如下:
被告穆增蕊抗拒运动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
她为了不连累丈夫,便提出与丈夫离婚。她一直以为母亲仍活着。母亲是她的精神支柱。为了母亲,她必须活下去。这成了她唯一的心愿,也是支撑她生命的唯一力量。她说她完全是为母亲而活着,为了母亲,她要好好表现,争取减刑。她除了努力完成劳改工厂的定额指标,还发挥她的专长,为监管人员的家属和牢友看病。由于“改造”得好,她的刑期由无期改为有期徒刑。1979年,文革结束三年后,她突然被宣布无罪释放。
出狱后,穆增蕊才知道母亲早已去世,才知道母亲去世前遭受的非人待遇及痛苦。实际上,她和她母亲被抬到医院后,医院完全没有救治她母亲,因为她母亲属于“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不给治疗,就这么又给抬了回去,腿脚折断、内脏受伤出血的老人在痛苦的煎熬中几天后去世。而穆增蕊因为是需要审讯的犯人,出于审讯的需要才给予救治。
她的精神一下子被彻底击垮。从此,她一直生活在“我到底有没有罪”,“我是不是杀人犯”的自我拷问中,头脑里不断地跳出来“是我亲手杀死了我爹”的提示。这种拷问和提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影随形地折磨着她,撕咬着她的心灵和精神而无法解脱。她总是不停地喃喃自问:“我杀死我爹,对不对?”她每问自己一次,就好像自己的颈动脉被割断,眼看着鲜血从血管里喷射出来一样痛苦。她说:“我怎么能过得了这个坎,怎么能原谅自己呢……我平时连一个蚂蚁都不敢踩死呀,怎么突然就下得去手了呢?”
穆增蕊出狱后仍然回到儿童医院工作。她力图克服精神上的压抑和折磨,争取回归工作。并努力补习荒废的业务。她对待工作依旧如故地那样忘我、认真、负责。每天可以看到她拖着残疾的右腿穿梭于一楼到五楼的8个病房,几乎天天工作14小时。
然而,熟悉她的同学和同事却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往日那个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穆增蕊已经不见了,再也回不来了!
1994年10月16日,南开中学成立九十周年纪念日,原班同学在校庆日相聚在学校参加班级聚会。这时,相距高中毕业已经39年了。
这次聚会,许多同学对穆增蕊表现出特别的关切。大家都发现她的身体不太好,神情抑郁、不爱说话,和在学校时判若两人。稍微了解一点情况的都私底下偷偷传说她一家在文革中跳楼自杀的信息,但是谁都了解得不确切、不具体,谁都说不完整、说不清楚,然而谁也都不敢问她本人,都不敢触动她内心那块隐秘的伤疤。
我也是听姐姐说,她是在那次聚会最后一次见到穆增蕊的。
据说,她出狱以后患了高血压。身体加心灵上的创伤损害了她的健康,长期的精神煎熬损伤了她的心智,最终她郁郁寡欢、沉默寡言地离开了人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虽然,她总算是无罪释放出狱了,然而,她失去的父亲、母亲谁能还给她?丧失亲人的痛苦和创伤能够得到弥合吗?十多年的冤狱所损失的青春有谁能够补偿她?她的身心遭受的摧残又该由谁负责?
那场号称“十年浩劫”的文革虽然似乎已经结束了,但是,噩梦真的已经彻底一去不复返了吗?
发动文革的元凶和罪魁,其僵尸仍然躺卧在天安门广场上,其画像仍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享受着歌功颂德、顶礼膜拜。
领导和组织文革的中共,今天压迫和压榨民众、与人民为敌的本质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吗?
由施害者来给受害者平反这究竟是幽默还是滑稽?
当年施恶的红卫兵忏悔和改正了吗?
今天的“一尊”习小丑居然自诩当代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居然要为文革正名,企图让文革借尸还魂、重新粉墨登场、再次祸乱中华!
当初被残害的无数穆增蕊们带着无尽的屈辱和痛苦走了,今天的赤纳粹/红卫兵/党卫军还想继续把中国民众当成又一批穆增蕊,残害我们的父母、摧残我们的儿女,我们能够容许吗?
转自:看中国
责任编辑:苏珊
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