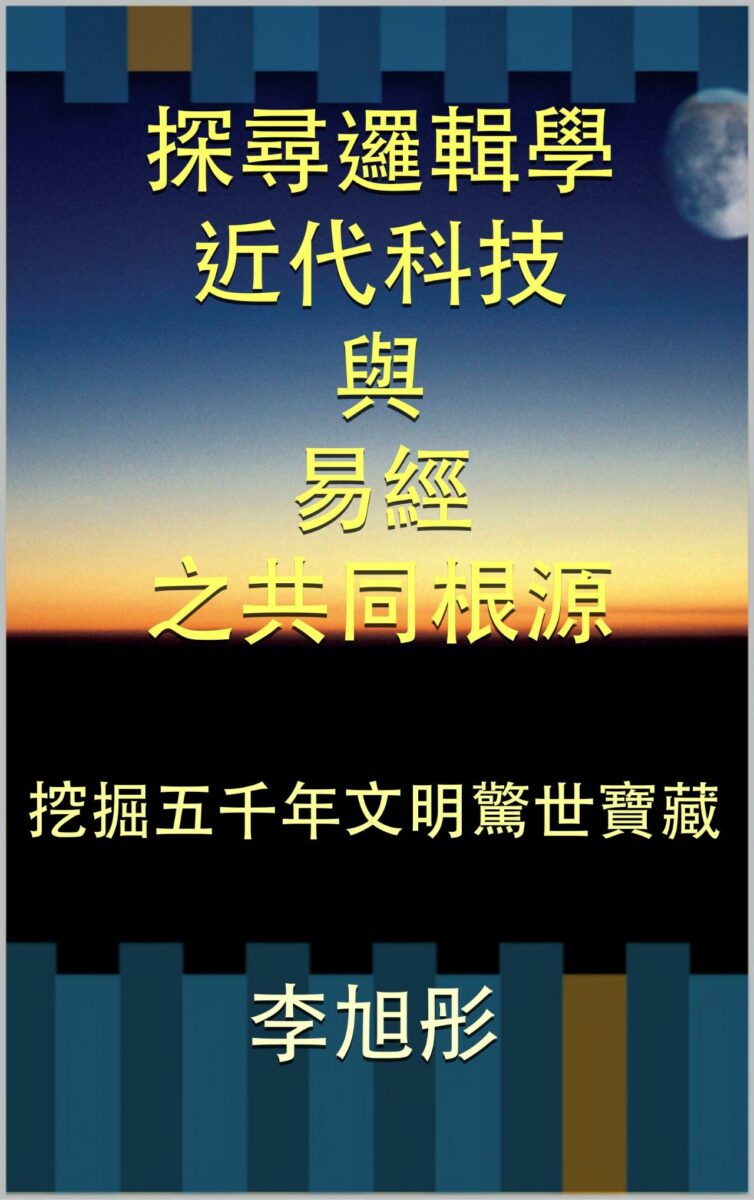戈里的文章翻译如下:
拜登总统将如何处理中国问题?美国在中共的奴工和酷刑集中营的问题上持何立场?拜登将如何阻止北京窃取美国的工作机会和知识产权?美国将如何阻止中共入侵台湾?
在这一点上,我们仍然没有看到美国新政府对华的任何具体政策声明。不像川普(特朗普)总统那样把与中共脱钩作为其指导政策,而拜登政府则没有提供这种总体政策构想。
而且,由于拜登政府还没有明确的对华政策,因此任何人都在猜测其政策可能是什么。但是,如果从拜登最近任命的政府官员来看,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能比前任政府更为宽松。
与中共的关系
拜登政府的一些内阁成员与中共有着密切或至少是重要的联系,当然,其中包括拜登本人。但是,还有其他几位与白宫亲近的人,他们与中共的密切关系也令人不安。
例如,副总统贺景丽的丈夫埃姆霍夫(Douglas Emhoff),据说通过其前律师事务所与中共有着长期的业务联系。《国家脉动》(National Pulse)报导说,该律师事务所与中共有关的中国企业密切合作。那真是不幸。但是,由于贺景丽担任副总统,她的丈夫或与他接触的中共人员都可能对贺景丽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美国政府。
拜登的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可能也有问题。《华盛顿自由灯塔》报导说,布林肯是咨询公司WestExec Advisors的联合创始人,该公司帮助美国大学从中共筹集资金,而又避免损及到五角大楼资助的研究经费。有人可能会想,根据美国国防法,把中共的钱引进到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中,五角大楼资助的研究经费将泡汤。但是对于拜登来说,显然不会。
东亚资深专家拉特纳(Ely Ratner)曾在新美国安全中心担任执行副总裁兼研究主管,后被任命为拜登政府五角大楼的中国首席顾问。拉特纳是拜登的长期助手,也许不是巧合,他还是布林肯在WestExec Advisors时的同事。 这也可能有问题。
然后是拜登的国防部副部长卡尔(Colin Kahl)。他是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高级研究员。该研究所与中国的北京大学有着深厚的关系。《华盛顿自由灯塔》报导说,后者是由中共前间谍头子邱水平领导的,并与在美国的间谍活动有关。
据《华盛顿自由灯塔》报导,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严重警告了与北京大学合作的“高风险”,因为北京大学与中共的军事机构关系密切。如果知道卡尔与中共有这么紧密的联系,那么卡尔的判断至少是有问题的。但拜登政府则不然这样认为。
前国务院官员、被拜登(Biden)选中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Linda Thomas-Greenfield)与中共的关系也令人怀疑。她是奥尔布赖特-斯通布里奇集团(Albright-Stonebridge Group)的前高级副总裁,该集团是一家在中国设有办事处的全球商业战略和商业外交公司,其高层主管包括“中共前政府高官”金立刚。
多元化和集体思维?
以上这些被拜登任命的人负责制定有凝聚力和有效的对华政策。尽管在性别和种族上都多元化,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却更加一致。
所有人的想法一致并不是优势,因为它容易导致集体思考。政策会议变成了回声筒,对事件的相同假设和分析,导致相同的解释和政策目标。当外交不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且本身就是目的时侯,其风险尤其大。
短期外交还是长期结果?
在拜登所经历的时代,美国的霸权或多或少是事实。这使美国的外交手段能够运用自如,美国的力量不言而喻,能被人清楚地知道。
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尤其是在中国问题上。北京的野心不是与美国分享权力,而是要取代美国。
但是拜登明白吗?他的顾问明白吗?还是他们认为与北京的关系会带给他们某种外交优势?可能是这种情况,特别是考虑到拜登政府把自己包装成比前届政府更聪明。
但是,与中共不寻常的金融接触是否会带来有利于美国的结果?还是会导致过度依赖于短期外交,而这些短期外交政策却使美国在挑战中共的具体行动中屈服于北京?
毕竟,挑战中共在政治上不容易,无论是在国内或国际上。回想一下,例如,川普政府在与中共打交道时很少依靠外交上的绥靖。相反,川普采用强硬的贸易政策将中共逼上谈判桌。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国内外受到严厉攻击。
像之前的奥巴马一样,拜登的做法基于过时的假设和多边的全球主义目标,而不是更明确的美国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华盛顿还没有宣布任何对华政策的原因。拜登最大的挑战似乎是如何向美国公众隐瞒不利于美国的对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