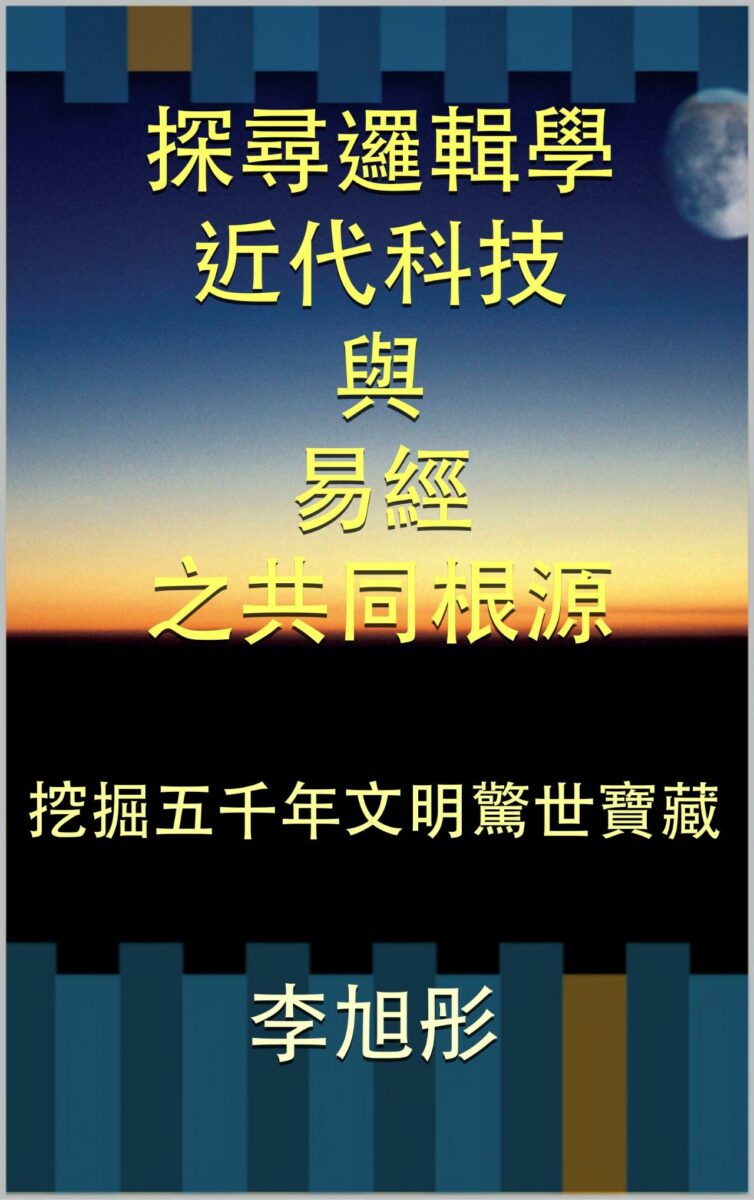刘江(右)在影片《闪闪的红星》中饰演“胡汉三”一举成名。(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刘江(右)在影片《闪闪的红星》中饰演“胡汉三”一举成名。(图片来源:网络图片)刚刚过去的五月一日这天,中国电影界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在电影《闪闪的红星》中饰演“恶霸地主胡汉三”的著名演员刘江去世了。他是电影界“五大坏蛋”最后一个去世的,不少人半诙谐半调侃的惊呼:“胡汉三再也回不来了!”
在中国电影界,素有“五大反派人物”之说,他们是葛存壮、陈强、方化、刘江、陈述,这五个人因多次成功饰演“坏蛋”而闻名。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电影故事里虚构或歪曲的脸谱化的坏蛋,都是按照中共的需要和政治标准整出来的,他们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坏蛋。尤其是:很多作品里刻画的所谓“恶霸地主”,反而都是被冤枉的好人。
刘江“把胡汉三演活了”
因为刘江刚刚去世,今天就趁着这股新鲜劲,从刘江在《闪闪的红星》里饰演的“恶霸地主胡汉三”说起。
《闪闪的红星》是一部儿童题材的电影,拍摄于1974年,当时正处于文革末期政治狂热的年代,电影界流行的一个口号是“上不上是个立场问题,拍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因此,对于摄制组和整个八一厂来说,拍这部电影更像是一项政治任务。当年10月1日影片上映后,按照中共的政治标准,影片获得了巨大成功,并在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评奖中获二等奖。刘江在影片中饰演“恶霸地主胡汉三”,通过他“出色的演技”,恶的够可以,霸的够邪乎,在乡里无恶不作,盘剥欺压百姓,吊打拷问年幼的潘冬子,残忍杀害潘冬子母亲……因此,凡是看过这部影片的人,无不被激起对地主的刻骨仇恨。胡汉三的一句台词“我胡汉三又回来啦!”成为当年流行语。
刘江演活了一个虚构的“恶霸地主胡汉三”,同时也影射抹黑了整个地方阶级,让中国人一提“地主”这两个字,就恨不打一处来。在中国民众中十分火暴的“斗地主”游戏,与这有直接关系。然而,中国的地主阶级是否真像电影说的那么恶霸那么坏?让我们从史实中寻找答案。
《收租院》与刘文彩不沾边儿
中共通过文学、影视与舞台作品,虚构了“四大恶霸地主”,他们是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周扒皮。经过反复灌输和渲染,这些“恶霸地主”臭名远扬,臭入人心。然而,谎言毕竟经不起时间的拷问,近些年来,“四大恶霸地主”已全部被拆穿。
四大地主中,刘文彩可排头一号。为了丑化文彩,1965年,在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泥塑了一组群像,象征农民向刘文彩交租子,还起了个名字《收租院》,大大小小共114个泥像,一个个栩栩如生,无言地诉说着“刘文彩的罪恶”。
1999年11月,笑蜀先生推出《刘文彩真相》一书,匡正了强加在刘文彩身上的污蔑之词,还原了真实的刘文彩。书中说:展示刘文彩罪恶的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完全都是按着“阶级斗争”的需要创作出的。
作者披露,庄园陈列馆为还原历史,曾派出专人采访了70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历过一年多奔波,水牢的人证、物证一个也没找到。据此,陈列馆向主管部门提交的《关于“水牢”的报告》说: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
1988年,四川有关部门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于是,地下室水被抽干,搬走铁笼,室门口挂上一块“鸦片烟室”的木牌,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
曾有一部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据史介绍了刘文彩兴办教育的事迹。当年刘文彩出巨资在家乡修建文彩中学,占地2000多亩。当时征地为使老百姓利益不受损失,刘文彩采用自己两亩地换一亩地。这所学校的规模和软硬件,当时在四川省乃至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
学校建成后,刘文彩“净身出户”,明确规定:校产归公,刘家后世子孙不得占有。刘文彩只在春秋开学典礼上露个面,简单讲那么几句,无非励志学生们发愤学习,将来报效中华民族。
刘文彩这人口碑好,又热心肠,逢年过节都要对贫困人家走访接济。因为他办事公道,乡邻纠纷也都乐意请他调解。此外,他还曾投资修建街道,现在未拆除的两条街道仍可想见当年的繁华。
“南霸天”与红色娘子军不搭界
陈强饰演的“南霸天”,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来者不善!他是《红色娘子军》里的大地主。戏中说他利用万贯家财,组织武装,与海南岛游击队为敌,后被“红色娘子军连”连长吴琼花(曾在南霸天家当过丫鬟)击毙。
据《海南视窗》报导,南霸天的人物原型,是海南陵水县一个地主,名叫张鸿猷。据张的孙子张国梅说,《红色娘子军》很多内容是虚构的。最大的破绽是在他爷爷死后4年,红色娘子军才组建。
张国梅披露说,当年拍电影的人见他家房子气派,又是大地主,选在这里拍电影真实。于是,就在他们家拍了几组镜头,又让老百姓到几里外的南门岭当演员,说是从南霸天家里的地道走到南门岭的。张鸿猷堂兄张鸿德的孙子张国强曾告诉记者,他是目前唯一健在见过张鸿猷的人。据他回忆说张鸿猷是个大善人,他没有欺压过百姓,家里也没家丁、枪支、碉堡。
据红色娘子军首任指导员王时香老人回忆说:“我们连长庞琼花,就是电影里的吴琼花。她是我们邻村的人,参军前我俩就是好姐妹,平时我们到镇上赶集就能碰到。她是贫农出身,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鬟,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这是和电影里不一样的。”陵水县史志办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张鸿猷没有血债,他家是教师世家。
从文人笔下“冒出来”的黄世仁
一出《白毛女》,演哭千万人!戏中说“恶霸地主黄世仁”,一心想霸占佃户杨白劳的女儿喜儿。除夕之夜,黄世仁强迫杨白劳卖女顶债,杨白劳被迫喝卤水自杀。此后,喜儿被抢进黄家,遭黄世仁奸污。喜儿与同村青年农民大春相爱,大春救喜儿未成,投奔八路军。喜儿逃入深山,过着非人的生活,头发全白。两年后大春随部队回乡,找到喜儿,伸冤报仇。两人结婚,过着翻身幸福的生活。
1945年,中共延安“鲁艺”把《白毛女》搬上舞台。尽管谁都没有见识过“黄世仁”和“喜儿”,但大家几乎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因为这出戏煽动仇恨效果一流,中共如获至宝,大力推广,一演再演。给人的感觉是《白毛女》这样的悲剧在“万恶的旧社会”司空见惯,地主个个都该千刀万剐!
然而,据《中华读书报》发表的“白毛女的故事”一文介绍,《白毛女》的题材来源于晋察冀民间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附近有座山,山里有个洞,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她扶正祛邪,法力无边,主宰人间祸福。抗战时,有些“根据地”的“斗争大会”常常开不起来,其原因就是村民们晚上去给“仙姑”进贡,使得会场冷冷清清。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题材,为配合“斗争”需要,把村民们从奶奶庙里拉回来,他编了一个戏曲剧本,主题是“破除迷信,发动群众”,此为《白毛女》的雏形。
不久,延安“鲁艺”院长周扬看到了这个剧本,决定由“鲁艺”创作并演出一部大型舞台剧,主题当然已经不是民间传说中的行侠仗义,而是反映阶级剥削给劳动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贺敬之很快就以诗人的激情和戏剧家的表现力,完成了剧本。
1945年4月28日,《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此后,一股《白毛女》旋风席卷延安,席卷陕北,席卷解放区,最终席卷了全中国。“文革”时期,几乎每年除夕,人们都会从无处不在的高音喇叭里听到《白毛女》的旋律——那是在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万恶的旧社会”。
只听半夜狗叫,哪有“半夜鸡叫”
周扒皮,这名字一听也是善者不来。小说《半夜鸡叫》中是这样描写这个“恶霸地主”的:他为了催长工们早早下地干活,竟偷偷摸摸半夜三更趴到鸡笼子口学雄鸡打鸣。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因为周扒皮这招儿太阴损缺德,读者们看后无不义愤填膺。其实,周扒皮的原型是今大连瓦房店市阎店乡一个姓邹的地主。据当地的老人说,根本没听说过半夜鸡叫的事情。
虚构故事时,还有些细节让人啼笑皆非。比如,描写周扒皮打开鸡笼子,划火柴去照……这种描写违背常识。试想,这些动作会让鸡受到惊吓,它还怎么打鸣呢?事实上,学鸡叫不必趴到鸡笼子旁边,也不用打开鸡笼子去看,熟门熟路要划什么火柴?即使把长工们早早赶到地里,自己不跟去监工,长工们躺在地头补觉,你又奈何?
后记
1958年,军旅作家冯德英的长篇小说《苦菜花》初版后,先后搬上银屏、荧屏、戏剧和话剧舞台,影响至少三代人。《苦菜花》塑造的人物:母亲、娟子、姜永泉,王唯一、王柬芝……都有生活原型。
2017年5月,笔者曾到山东乳山,《苦菜花》故事的发源地观上冯家村,实地调查这桩历史公案。历时20多天,通过多方探访求证,查阅历史档案,证实《苦菜花》中描写的第一大坏蛋王柬芝(真名冯鉴之)完全是颠倒黑白的一场冤案。事实上,冯鉴之家境富裕,他是当地一位名震方圆百里的大文人、大善人,在当时的烟台牟平一带,有“南有冯鉴之,北有张玉俭”之说。冯鉴之的后人想起诉冯德英,为冯鉴之讨公道,但慑于冯德英的职位(山东省作协主席)和人脉,而不敢为之。
今年五月一日,刘江走了。但不知他到了“那边儿”之后,当阎罗王翻开册簿,针对他饰演“胡汉三”帮助中共抹黑地主这件事儿向他问罪的时候,刘江会不会悔不当初。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美莲
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