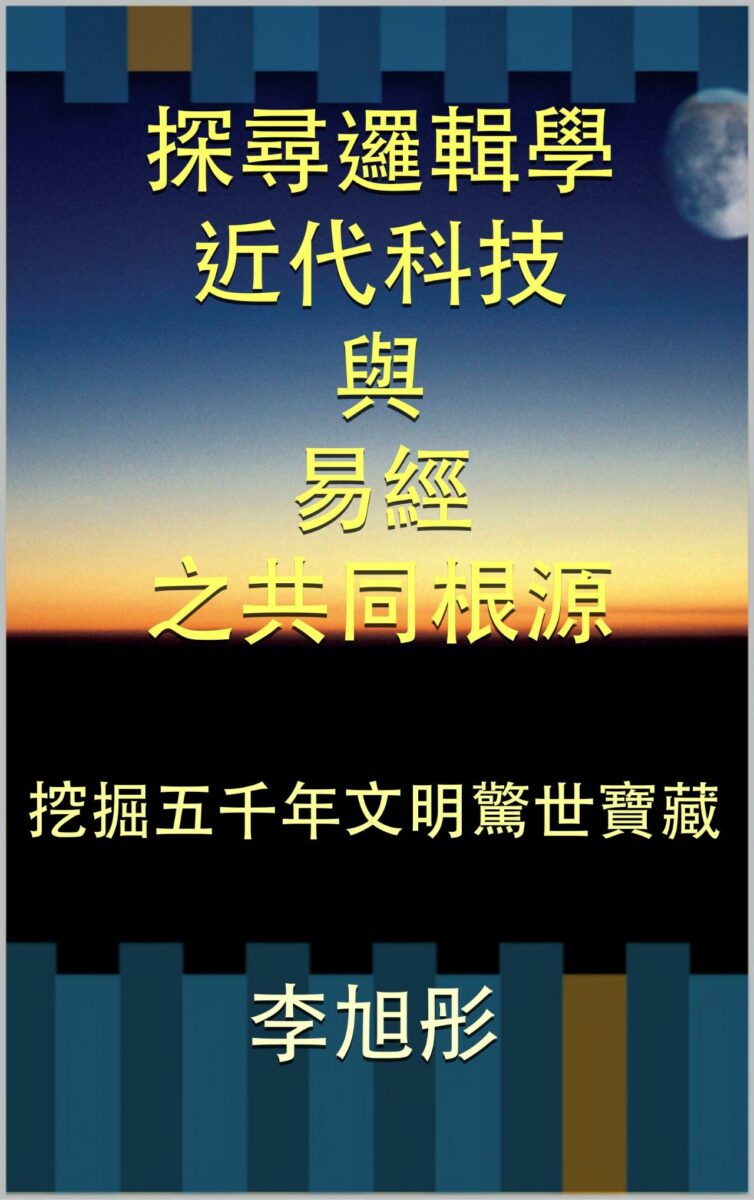【2021年1月17日】在你的人生际遇中,你能提供给他者的精神养分是什么呢?你给予人的细节,是温暖还是伤痛呢?是贪得无厌的索取,还是一边抱怨一边付出呢?是喋喋不休的斤斤计较,还是胸有城府步步为营的貌似贤良呢?对于你最亲近的人,你的存在,是一个珍贵的礼物,还是一场灾难呢?
在宝玉挨打的那一回,宝玉因为记挂黛玉,想让人去看看她,书里写得十分直白:“满心里要打发人去,只是怕袭人,便设一法,先使袭人往宝钗那里去借书。”袭人走后,宝玉便让晴雯去看看黛玉,说,你去看看林姑娘在做什么,她要问,你就说我好了。
晴雯就说了:“白眉赤眼的,你让我去做什么呢?好歹有句话,有件事吧?”她讲话总是跟燃烧的炭火似的,不时就炸一个火星子。宝玉说,没什么话,也没什么事可说。
晴雯说,那你总得有个由头吧?送点什么东西,差使我去取个什么东西也行啊。宝玉想一想,就拿起手边自己的两条旧手帕,让她送过去。晴雯托着两条旧帕子来到潇湘馆,只见屋里漆黑,不曾点灯,黛玉一个人在帐子里头躺着。可以想见——黛玉天不黑就躺下了,那又是一个以泪洗面的寂寞黄昏。从晴雯那里接到这旧手帕,黛玉是很感动的,书中用一个词“神魂驰荡”来形容黛玉的心情。这样的事,宝玉本能地回避袭人,却特意交给晴雯去做。他们之间,是有一种懂得的,而袭人对宝玉的管制,正在发挥作用。
袭人,是另一种属性的女性,一如我们前头说过的,她是俗世的、母性的、贤良的,同时又是狭隘的,步步为营的。晴雯的缺心眼儿,在于她会毫无顾忌地逞口舌之快,骂骂那些小丫头。而袭人,上上下下都喜欢她的行事得体周到,贾府里,唯有两个老妇人冷眼旁观袭人,且偶有惊人之语。一个是宝玉的奶娘李嬷嬷,另一个便是贾母,说的都是袭人“托大”,意思是平日里做小伏低,隐忍贤慧,是见机行事,等到羽翼丰满时,她是会露出自高自大的。但这种微妙的衍变,只有贾母和李嬷嬷这种饱经世故,洞察人事的老年妇女,她们练就的一双火眼金睛,才看得出个中端倪。即使是王夫人,能看见的只是袭人对宝玉的忠言死劝。所以,《红楼梦》这本大书,你真的是要历经人事,才能逐渐体察那些看戏吃酒,家常闲话背后的人心冷暖,才会逐渐地懂得曹雪芹,懂得人性的善恶同在。
袭人事事都替宝玉作主。譬如过端午节后,史湘云来贾府小住,她就会去请湘云给宝玉做针线,借口是宝玉的穿戴不肯要外头的针线,所以只好自己动手,可是自己根本忙不过来,于是来托请湘云。但是我们在“病晴雯勇补金雀裘”那一回看到,晴雯的针线是特别出色的。但她精巧的针线手艺和宝玉之间,隔着一个袭人。所以她不去动那些针线活儿,袭人还需要去隔山隔海地求助史湘云。
也因为这个针线活,袭人也有了更多指点人物的底气,譬如史湘云曾计较,她给宝玉做的香囊,黛玉做了些璎珞穗子缀在上头,一次林黛玉和宝玉怄气时,拿剪刀把穗子剪了,香囊自然也不能幸免。史湘云就说了——她既然剪,那就自己去做呗,干嘛老让我做呀?我的东西又不是给他俩怄气用的。袭人听湘云如此说,喜笑颜开地赞美湘云,说史姑娘最是心直口快,又补了一刀,貌似公允地评价林黛玉说,林姑娘嘛,去年一年就只见她绣了个荷包,今年呢,还不曾见她拿过针线。
旁观者清,宝钗身为那个旁观者,为这些针线活,就指点袭人说,你不要全指望史姑娘头上呀,听她的口气,她家里的针线,素来都是她在做,你再求到门上,她又不会推辞,岂不是更加受累。袭人恍然大悟说,难怪上个月烦请她打十根蝴蝶结子,好久才送来,还说等住进来了,再打得更匀净些。但袭人却有她的理由:“偏生我们那个牛心左性的小爷,凭着小的大的活计,一概不要家里这些活计上的人做。我一个人,又弄不开这些。”宝钗就说,我来替你做些罢。袭人很是感激,表示晚上自己亲自送过来。所以,侍候宝玉穿戴的这些针线活,里头的心思是很多的。是恃娇恃宠的独占把持,还是醉不在酒的托请与帮忙,在袭人和晴雯这些相同身份的丫鬟们之间,里头还有砌墙式的隔绝,防范和护卫利益,以及晴雯等为表明立场,退避三舍的不予插手。看到这里,你就会格外懂得林黛玉的好处,她是全然不沾染这些的。她好读书,案几上都是书,一如刘姥姥赞美的,看着以为是读书的公子哥儿的房间,她虽然懂针线,也不动针黹,也不以此来彰显女性的贤德,她看着比谁都小心眼,然而,她只和宝玉一个人小心眼,她计较的只是他的真心,从来不是现实利益和关注度。她对人生的姿态,有如不系之舟,有一种不牵不绊的洒脱。
在我们反复提及的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宝玉对黛玉诉说的那一句“你放心”,他说,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才有这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那林黛玉听了这番话,流着泪,回身走开了。宝玉上前拉住她说:好妹妹,你且站一站,我说一句话再走。黛玉一面推开他的手,一面拿帕子拭着泪道:有什么可说的呢,你要说的话,我早知道了。说着便头也不回地去了。
宝玉却只管在原地站着,袭人看见他和黛玉站着说话,以她一贯的公事公办赶上前来送扇子。因为整个前八十回,但凡宝玉和黛玉凑到一块,必然会有袭人上前来叫走宝玉。她这个袭人,也不是徒有虚名,时常突兀来袭是她擅长的。
呆子一样的宝玉,根本没意识到黛玉走了,而是顺势拽着那只袖子,倾诉道:“好妹妹,我的这心事,从来也不敢说,今儿我大胆说出来,死也甘心!我为你,也一身的病在这里。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掩着。只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等到他被袭人推醒过来,羞得满面紫涨,夺过扇子就跑了。
其实这一幕仔细体味,你真的会很同情袭人的。对于宝玉和黛玉,这是彼此互证心意的一刻。然而,对于袭人,是人生之中至为残酷的一刻,这种残酷程度,远远大过日后她离开宝玉,改嫁他人时的无奈。
*********
《红楼梦》前八十回里,袭人是大观园里唯一真正和宝玉有过肌肤之亲的那个女孩子,她也是把宝玉当作终身依靠的。她知道宝玉将来是要娶正房娘子的,她将来是要侍候这夫妻二人的。然而,常识是一回事,真情是另一回事。偏偏是她,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来倾听宝玉对黛玉的那一番倾诉肺腑的山盟海誓之词——人生的残酷之处,在袭人这样懂得保全自己的人这里,施予的痛感也是一样的,一点都不因为她比别人更周到、更世故、更圆滑,而减少受伤。
在黛玉和宝玉之间,有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彼此体贴入微,契合无间的心灵联系,那个空间场,是外人根本进不去的。如袭人这样贴身照顾宝玉三餐一宿的人,每每公事公办地,走来打断宝玉和黛玉,把宝玉带走,饶是如此,她也是进不去宝玉和黛玉的精神世界,她那些微妙的干扰也从来改变不了宝黛之间的心意相知和默契,以至于黛玉这样细腻敏感的人,从来都不曾注意到袭人对她持有的微妙的敌意——因为黛玉心里没有这些争斗。
袭人回家奔丧的那段时间。有一次,黛玉叫住了宝玉,却又无话可说,于是就问:袭人什么时候回来?可见,袭人从来都不是黛玉的敌人,黛玉对她,一直都是有一种亲切感的,而且是毫无妒忌心的。
袭人和宝钗之间,在气场上远比和黛玉来得契合。她们是相同类型的女子,审时度势,谨言慎行,善于自保,所以,她们之间是一个彼此探究,逐渐认定的过程。如果让喜欢掌控局面的袭人去为自己和宝玉选择一个将来的宝二奶奶,那么袭人一定会择定宝钗。所以,宝玉以为,自己这一生定然是和黛玉、袭人相守在一起的,那是他的天真和无知,他根本没有感受到,彼此内心的距离是多么遥远。
袭人和宝玉是彼此交付了童贞的人,可在宝玉的精神世界里,她从来走不进去,她只是站在外头,数落他的种种对世俗陈规的反叛,她的种种规劝和死谏,从来都是和宝玉的价值观相违背的,宝玉也从来没有把她的话真正入心。只是因为宝玉是个好脾气,所以由着她指教唠叨。而恰好是袭人,而不是别的任何女性,听到了宝玉对黛玉那一番掏心掏肺的告白,我想,任何女性经历这种情形,都会感受到深重的伤害和刺激。然而你能说袭人就是无辜的吗?她的苦头就是宝玉强加予她的,而不是她自找的吗?又或者,宝玉就是我们当下语境里的那个很渣很渣的渣男吗?
*********
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对于我个人而言,是一个不断地破除我脑中的现代观念、女权观念加于思想桎梏的过程。身为一个女性,如果你持有很多女权观念,读这本书时,你是常常会被触怒的。因为看起来里头充满了男女的不平等,书里的婚恋观念,也和我们如今的社会形式格格不入,但是,《红楼梦》里头的人际关系、男女问题,在今天依然不曾过时,因为从古到今的人性是相通的,所以,《红楼梦》这本书中的男女关系、人际关系,放在我们当下的语境里,还是有对应意义,值得讨论的。
首先我们需要真正意识到——人的心灵是丰富的,虽然我们的灵魂在神眼里是平等的,但精神生活绝对是分层次的。这也就是袭人她进不去黛玉和宝玉之间的世界的根本原因。而袭人和宝玉之间,其实说白了,肌肤之亲,朝夕相处,三餐一宿都在一起,我们凡俗的婚姻生活,也就是如此了吧。在他们之间,也是有话说的。譬如袭人从王夫人那里得了额外拨出的二两银子的月例,她不声张,却等到夜深人静,四下无人时,告诉给宝玉,宝玉很高兴,说,你平日动不动就说要回家去,这下你可是回不去了吧?那脂砚斋在批注这个情节时,就点评说,这一幕很有长生殿的味道,也是夜半私语时。那袭人也会很操心,宝玉送礼回礼的事情,如吃了史湘云的螃蟹宴,参加了宝钗哥哥薛蟠召集的聚会,她都要去问宝玉,要怎么个回礼。她也会操心怡红院的物器,有一次要给史湘云送东西,要用漂亮的缠丝白玛瑙的碟子,就问起来,这个碟子怎么不见了,晴雯回答说,是宝玉给三姑娘探春送荔枝,选了这个碟子,因为红配白,相宜好看。那她要操心,去把这些东西取回来,别失散了。这些琐碎家务,在我们现代的婚姻生活中,说起来都算得上主妇的职责。而这些家长里短,宝玉和袭人也是能说到一起的。
但是在黛玉和宝玉的精神世界里,袭人就是完全进不去的。所以,她每每要规劝宝玉读书,引宝玉说话,宝玉一旦说起那些生死的话题,她就不接话了,一句都接不上,她对这些话题也没有兴趣。譬如有一次宝玉说起生死,说要是自己这会儿死了,姐姐妹妹的眼泪为他而落,漂成一条河,把他送到天尽头,随风化成灰,那就算他的死得其所了。袭人一听这些疯话,赶紧装作已经睡着了,宝玉也就打住不往下说了。而这些话题,宝玉和黛玉是一直能对谈的,是没有任何避讳的,他们在最终极的精神探索中,一直是比肩同行的。
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里头有一句话:人是一夫一妻的,人也是一夫多妻的。体味起来很有嚼头,很隽永,也很能写照几千年来男权社会的男女关系。一夫一妻,大概就是我们说的灵魂伴侣吧。在精神上你和一个人能沟通,有着相同的心意,对生命的相同定义,相同的探索等等。如果是同性,两个人可以做至交,知己,是异性,你们是夫妻,伴侣,这种关系是一个坚如磐石的世界,大抵是不会变节变心的。但是,一般人是没那么幸运的,或者,也不需要那么多精神,饮食男女,食色性也,宝玉和袭人,以及俗世众人的男欢女爱,大抵多在这一个层面上吧。放在书中,我们可以说,宝玉和袭人,以及他房里的那一群丫鬟,又譬如贾琏和王熙凤、平儿、后来的尤二姐,是一夫多妻的,是在一个契合的平台上,很容易成就的一种男女关系。这种关系也很亲切很生动,有家常日子,有岁月相伴的常情,年长日久形成的默契。然而,如果不是精神的契合,到末了也只有这么多。就如同最后袭人会离开宝玉,因为,宝玉在她那里,最大优点也就是她素来熟悉的温柔体贴。更多的,她不了解,进不去,也视为异端,从没打算进去。所以,她能离开,能走得开。没有了大观园,没有了怡红院,失去了富贵青年公子所有的种种,宝玉这个人,在袭人或者俗世的眼里,是没有什么独一无二、天下无双的价值的。所以袭人对宝玉,永远不可能等同黛玉对宝玉。
黛玉会为宝玉流泪,年年岁岁,朝朝暮暮,直到哭干了所有的泪,早夭逝世。他们是绝对的知己,从天上到人间,彼此互为印证。一个人死了,另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就坚持不下去了。一切人的形式,都不能在他们中间起作用的,死亡可以把他们分开,但是死亡无法改变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深情,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的心灵域野上的最终极的笼罩和拥有。因为这个人在的时候,她印证得这个世界很是清晰╴╴天地万物、人间亲伦、花开花谢,在宝玉眼里,一切都是成立的。但若是这个人不在了,这个世界在宝玉眼里,就是一个梦境,就如同走错了房间一样,他在这里就没有任何的留恋和牵挂,而是想方设法要脱离红尘,要超脱这一切。
所以,我们真的不能愤怒地聚焦在宝玉到底有多渣,处处留情——我们身为现代女性,需要的是真诚和理智,去面对真实的人性,而不是用一个想当然的女权的框架,去要求人性应该这样或者那样,又因为人性远比我们认为的要复杂,事实和理想总是不符,所以我们女性时时会被触怒,会受伤,会心生怨恨。这里我们不是说,大清朝都亡了一百多年了,我们重新讲起了君臣父子,妻妾尊卑之道。我们说的是,你要去真正认识人性——女子的属性,男子的属性。在心灵的层面上,人有对真理和智慧的渴求,人也有七情六欲的本能。那么我们身为女子,身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命,在你的人生际遇中,你能提供给他者的精神养分是什么呢?你给予人的细节,是温暖还是伤痛呢?是贪得无厌的索取,还是一边抱怨一边付出呢?是喋喋不休的斤斤计较,还是胸有城府步步为营的貌似贤良呢?对于你最亲近的人,你的存在,是一个珍贵的礼物,还是一场灾难呢?
这也是我们阅读《红楼梦》收获之一,那就是我们最终要得见自身,在天地之间,是驯服的而不是叛逆的,由此去察省优劣。人犹如一粒芥子在天地之间,当你意识到你的微小,人山人海的拥挤,你目之所及的生命的丰富、繁多、炫目的光彩,你才会有本真的谦卑和柔顺,去面对人生。